《大西洋月刊》刊登的这篇最新研究分析指出,人体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感染新冠,或者注射新冠疫苗的经历。这种“抗原原罪”给新冠疫苗研发和注射,以及民众的未来防护提供了新思路。
在新冠疫苗在美国上市的两年多时间里,基本配方只改变了一次。但与此同时,病毒已经产生了五个变种,它们各自获得希腊字母名称,然后是各种奇怪的奥密克戎亚变种,每一种似乎都比上一种传播得更快。
疫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重新配制,但就是无法跟上这种似乎每周都在重塑自己的病毒。

但是新冠的进化冲刺,可能不是免疫力在过去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人的身体似乎固定在它通过注射或感染的第一个病毒版本上。这种对过去病毒的专注,研究人员称之为“抗原原罪”,这可能使我们的防御系统不能很好地适应流行的变体。
最近几个月,一些专家开始担心,这种“抗原原罪”现在可能正在破坏更新的疫苗。他们认为,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无法从与当前病毒变体完全匹配的新冠疫苗中获得多少保护。
最近的数据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
人体的这种与病毒或原始疫苗的历史接触,似乎打造或抑制了人们对二价疫苗的反应(bivalent vaccine,指升级版的二合一疫苗,能同时对付原始毒株和变种)。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詹娜·古斯米勒告诉我, “我对此毫不怀疑”。
人体的免疫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没有产生以奥密克戎为重点的抗体,除非免系统先接触到更新的疫苗,才可能会产生这种抗体。
但这种固执也有一个好处。免疫学家和传染病模型专家凯特琳·戈斯蒂克说,他曾用流感研究过这种现象,“抗原原罪”是重复感染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会变得更温和。
戈斯蒂克说,“这是能够创造免疫记忆的一个基础”。
这不仅仅是基础生物学的问题。身体对这种冠状病毒强大的第一印象,可以而且应该影响到我们如何、何时、多长时间重新接种疫苗,以及用什么来接种。更好地了解这些病毒印象的程度,也可以帮助科学家弄清楚为什么人们能够(或不能)抵御最新的变种,以及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化,他们的防御系统将如何应对。
关于“抗原原罪”,最糟糕的是它的名字。这在技术上要归咎于小托马斯·弗朗西斯,这位免疫学家在60多年前,注意到人们在童年时经受的最初的流感感染,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后来的病毒株的抵抗力,因而创造了这一短语。
洛克菲勒大学的免疫学家加百利·维克多拉说:“基本上,你在人生中第一次得的流感,是你的身体一直在准备对抗的,当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同的毒株来敲门时,这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抗原原罪”听起来可能就像一个痴情的青少年对前任的思念,或者一个从未从免疫小学毕业的学生。但从免疫系统的角度来看,永不忘掉你的第一次遭遇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与病原体的新接触让身体猝不及防,而且往往是最严重的。
因此,固执己见的防御反应是很实际的,增加了击败下一次同样入侵者出现的可能,其将被迅速地识别和消灭。维克多拉告诉我:“拥有良好的记忆并能够迅速提高记忆力,有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身体确保自己不会被愚弄两次。”
人体记住老病毒的这种恩怨情怀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微生物蜕变成新的形式时,就像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经常做的那样。病原体不会一下子重塑自己,所以免疫细胞如果对熟悉的病毒片段感兴趣,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可以扼杀足够的入侵者,以防止感染的最坏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与这个季节最突出的病毒株并不完全匹配的流感疫苗,通常仍能很好保护人们免受重症或死亡。
古斯米勒告诉我,在人体真正失去保护之前,病毒的变化往往不会有那么剧烈。她说,对于新冠来说,回旋的余地应该更大,因为亚变体往往比流感不同的毒株更加相似。
由于免疫记忆可以提供很多积极因素,许多免疫学家倾向于改变“抗原原罪”这一短语消极和怪异的道德暗示。
亚利桑那大学的免疫学家迪普塔·巴塔查里亚说:“我非常非常讨厌这个词”。相反,巴塔查里亚和其他人更喜欢使用更中性一些,如印记,让人联想到小鸭子抓住自己发现的第一个母体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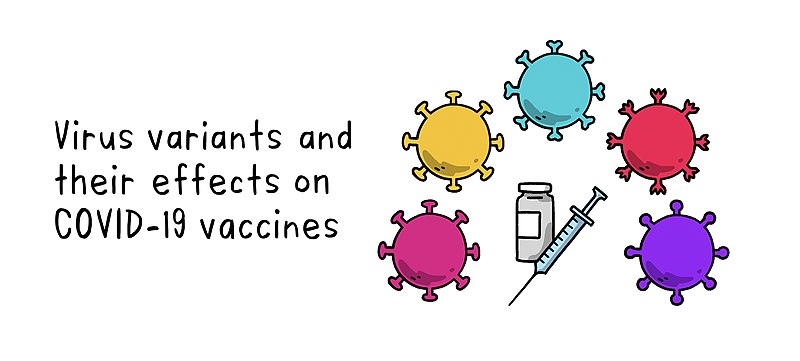
埃默里大学的免疫学家拉菲·艾哈迈德解释说,这不是什么奇怪的免疫学现象,这更像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说明一个适应性强、功能高的免疫系统会做什么,而且根据情况,它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最近的流感爆发展示了这两种情况中的一小部分。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许多老年人通常更容易受到流感病毒的影响,但他们对上世纪末的流感病毒表现得比预期的要好,因为他们在年轻时曾接触过相似的H1N1,这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背后罪魁祸首的衍生品。
但是在随后的一些季节里,H1N1病毒使中年人不成比例地患病,他们早年的流感记忆可能使他们失去了保护性反应。
这些成年人身上一直在追溯历史的免疫系统,可能不仅优先放大了对不太相关的病毒株的防御性反应,可能还抑制了对新病毒反应的形成。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免疫学家斯科特·亨斯利说,在过去的变种和毒株上训练有素的老牌免疫细胞,往往比新细胞更快上手。而且,有经验的士兵数量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排挤新兵,这使他们失去了可能积累的战场经验。
如果较新的病毒株最终回来重复感染,那些经验较少的免疫细胞可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许会使人们比原来更容易受到伤害。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形式的病毒印记,现在可能正在新二价冠疫苗中发挥作用。一些研究发现,与原始配方疫苗相比,以BA.5为重点的疫苗在产生奥密克戎靶向抗体反应方面充其量是中等有效的,而不是一些人可能希望的彻底击败病毒。
加百利·维克多拉的实验室最近在小鼠身上的工作支持了这一观点。B细胞,即抗体的制造者,似乎确实难以摆脱它们从第一次接触中得到的新冠刺突蛋白的印象。但这些发现并没有真正困扰维克多拉,他欣然接受了自己的二价新冠注射。
他告诉我,对一种新疫苗的反应迟钝是存在的,而且与第一针相比,第二针的配方越是陌生,就越能看到新战士参与战斗。
他说,人体仍然在增加新的反应。当变得相关时,免疫系统会重新振作起来。新冠病毒是一个快速进化者。但是免疫系统也会适应。这意味着接受二价疫苗的人,仍然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奥密克戎变种的影响。
历史上的流感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
许多被最近的H1N1病毒感染的中年人,可能没有被陌生的病毒攻击过,但随着免疫细胞不断与病原体进行斗争,戈斯蒂克告诉我,身体“很快就填补了空白”。虽然有人想把病毒印记看作是一种运气,但古斯米勒告诉我,这不是免疫系统的工作方式,偏好可以被改写,偏见也可以被消除。
“抗原原罪”可能不是危机,但它的存在确实表明,我们在优化疫苗接种策略时要考虑到过去的偏见。有时可能需要避免这些偏好,在其他情况下,应该积极接受这些偏好。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免疫学家需要填补他们对病毒印记知识的一些漏洞:印记发生的频率,它的运作规则,什么可以巩固或减轻它。在流感病毒中,这种模式已被研究得最为透彻,但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例如,第一次感染或接种疫苗是否导致印记更强?
科学家们还没法肯定,儿童由于其激烈但易受影响的免疫系统,是否更容易或更不容易被他们的第一次流感病毒所困扰。研究人员甚至还不确定第一次接触后的重复感染,是否会让病毒更深地嵌入一个特定的印记。如通过同一疫苗的多剂量注射,或同一变种的再感染。
艾哈迈德告诉我,多剂量的疫苗可能会加剧早期的偏见,这看起来确实很直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样的原则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也许多次接触新版本的病毒可以帮助打破一个旧的习惯,并促使免疫系统继续前进。
最近的证据表明,以前感染过早期奥密克戎亚变种的人,对以BA.1为重点的二价疫苗,比那些以前从未遇到过这个的人反应更强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亨斯利现在正试图弄清楚,对于那些在感染了许多奥密克戎亚变体之一后,又注射了基于BA.5的二价疫苗的美国人来说,情况是否也是如此。
艾哈迈德认为,给人们打两针更新的疫苗,也可能使身体摆脱旧的病毒印记。他指出,相比在这种混合中加入感染,这是一种更安全的方法。几年前,他和他的同事表明,第二剂特定的流感疫苗,可以帮助改变人们的免疫反应比例。
对大多数人来说,今年秋季注射二价疫苗的第二剂可能并不实际,也不讨人喜欢,尤其是现在BA.5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如果明年秋天的配方与BA.5有重叠,而与原来的变种没有重叠的话,稍微推后去注射略微不同的疫苗仍然可能是有帮助的。

巴塔查亚说,保持疫苗剂量的相对间隔可能也会有帮助,例如每年一次,就像流感疫苗一样。
他最近的研究暗示,如果给更多的时间,身体可能会“忘记”旧的变体。随着针对以前的感染和注射产生的抗体逐渐消失,疫苗成分可能会在体内徘徊,而不是被以前的免疫力压制。这种略微延长的停留时间,可能会给免疫系统的新成员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产生奥密克戎特定的反应,虽然数量较少,吸收也较慢。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研究人员可能有一天会对病毒印记有足够的了解,以便在他们选择和推出新的疫苗时考虑到它的微妙性。例如,流感疫苗可以被个性化,以便根据出生年份来确定婴儿首次接触的菌株,新冠疫苗的剂量和感染的组合可以决定下一次注射的时间和成分。
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操作,戈斯蒂克告诉我。经过三年来不断变化的新冠病毒和波动的公共卫生方法,很明显,不会有一种单一的疫苗配方能同时适合所有人。
亨斯利告诉我,即使是提出“抗原原罪”这一概念的小托马斯·弗朗西斯,也不认为“抗原原罪”是完全负面的。根据弗朗西斯的说法,“原罪”的真正问题在于人类错过了在儿童时期一次打上多种菌株烙印的机会,当时的免疫系统还是一片空白,而现代研究人员很快就可以通过开发通用疫苗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对病毒的第一印记的依赖可能是一个不足,但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身体尽早熟悉多样性,给它一个更丰富的叙述,以及应对未来许多威胁的记忆。


